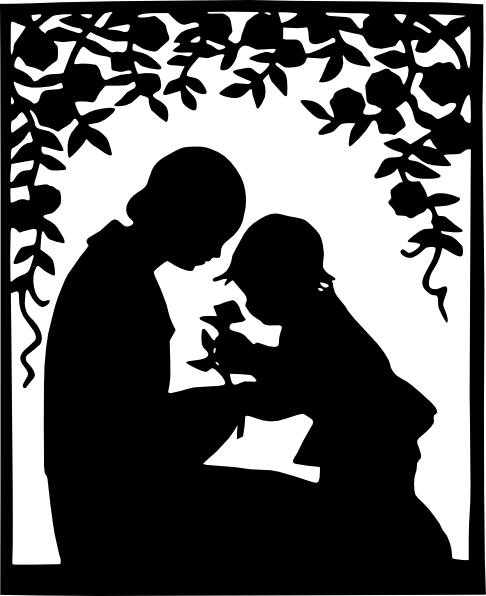YN的自我介紹:熱線義工。一個受著直覺與好奇心驅使卻又常被主流價值觀拉扯住的女生,還在摸索如何在充滿混雜聲音的社會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存在樣貌與位置。
預期之內之外的「禮物」
25歲,人生好像正要振翅高飛的階段,這時候的你會在做些什麼呢?
出國念書取得越洋碩士的洗禮加冕嗎?還是打工換宿一下,體驗人生的自由與寬闊?也可以是開始找第一份工作並且抱怨大學新鮮人才如壁紙般的不值錢;或者,面對老天爺給我的第一份大禮物。
其實生離死別是一個必然存在的議題,這我都知道;未來的某一天,爸爸媽媽終將離我而去,未來的某個時候,我終將面對自己不再是個小孩,會是這個家或是某個家的主要角色,或者我終將成為家人的臂膀,像是一棵煥然新生的大樹,成為鮮綠且強健的存在,而且成熟穩健。
但是關於「未來」,誰給過你標準尺規了呢?
大學畢業的暑假,找了第一份意外的新工作,在國中擔任代課教職。全新的教職領域,青少年族群,教材內容只有學期三分之一份量的輔導課,比學生還菜的新老師,okay,硬著頭皮我可以。其實沒有什麼太大不了的,只是在這個時候,老天爺還是想要送我一份大禮物。
因為阿公、姑婆相繼的過世,家人不放心的狀態下只好讓阿嬤北上跟我們同住。連續的失去最親近的陪伴者的阿嬤,就在這一年開始了老年失智的退化狀態。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人就是會老,就是會慢慢的到來;我想我們都是這麼準備好的吧。過了半年,我的媽媽說醫生檢查出她的體內有顆大腫瘤,她有了卵巢癌。這其實也還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人生來就是會有些身體疾病,年紀已來到六十的老媽不可能在不停操勞的生活狀態下都沒有病痛,就是會慢慢的到來;我想我們也是都這麼準備好的。
其實關於未來,我想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想像和演練過程。可是當未來悄然到來的時候,你以為的準備好,似乎都還是不及格。
我說,面對自己的媽媽生病了,阿嬤失智了,我依然可以在學期結束後的暑假跟著朋友去一趟為期兩周的遠行嗎?如果媽媽此時需要我陪她去一趟門診,但卻因為新手老師面對一天近乎四、五節課的課表,但眾人皆表現想幫卻幫不上忙的調課請求的時候,所以婉拒了媽媽的需求(這只是一個小忙吧),我是不是太自私的表現呢?如果周末的夜晚想和一群朋友出門喝酒聊天到深夜,那會不會對老媽來說是種諷刺呢?如果朋友邀約你一起去參加各種NGO團體的志工服務活動,會不會覺得家裡的阿嬤我都沒有那麼殷勤了,還去服務別的老人家,這樣對嗎?如果把所有的照顧工作都給外勞了,那我還能做些什麼呢?別人的爸爸媽媽都在一個瀕臨退休的年紀,為什麼我的媽媽要在這個時候生病呢?如果我可以早點出生,像姊姊一樣,是不是會比較容易且公平呢?如果我想說說我的苦,有沒有人是聽得懂得呢?
關於自己的有限與期待的無限,總有個無法平衡的天秤一直在擺盪,擺盪。
但我又說,遠在美國工作的姊姊沒辦法時常回來,她會自責感到虧欠嗎?還是其實這樣是最剛好的距離呢?老爸假日寧願出門打球也不願意帶老媽或阿嬤去郊外走走,他是不是很自私呢?其他的叔叔、姑姑,住在國外那麼遠,他們是不是就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般的理所當然的插手不管了呢?為什麼老爸總是把老媽想要他陪伴的需求變成我跟他的共業呢?這個公式怎麼寫出來的?為何我總是推算不出來?
喔,親愛的,我真的頭好痛,我總是找不到這些計算題的答案,也沒有最後的解答區,我都翻不到;你能告訴我你看到解答寫了些什麼嗎?
我想說,你面對一個自己以為還不會失去的人可能即將在你的面前生命凋零,你如果願意,其實你會想做得事情有好多、好多,但你終將在某些時刻發現,原來自己如此渺小且無能為力。
為什麼不能多給點陪伴?因為每當我去陪伴媽媽的時候,我可以從她的言語和眼神裡感覺到,她渴望在這裡的人是我爸而不是我;當我嘗試逗樂阿嬤的時候,她總是最後問我:「你可不可以開車載我去找你大姑?或是你帶我回屏東,好不好?」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了,在這些不斷、不斷的接觸過程中,我成為了替補品,我成為了工具,我的關心與愛成了地上的影子--不是渴望的主體,卻是必須隨時存在的角色。在有陽光的時候,影子就會在;在燈光微弱的時候,即便沒有人注意你,親愛的影子,你依然要堅守崗位。
你問,人在什麼時候需要勇敢?我想是當自己無比脆弱且無助徬徨的時候,你需要「勇敢」讓自己面對一切的未知,交付機會於嘗試的手中。
面對自己從社工系畢業,身邊不乏一些社工界的朋友和醫療體系工作的朋友,姊姊又是醫學大學畢業的,其實我們應該有不少的醫療和身體照顧的資源可以給我媽媽嘗試,但她都一一回絕了。記得在老媽倒數幾次的看診過程中,我無助且憤怒的掉了眼淚。我看著天空,我問著我自己和那個無聲的誰,是否我還不夠努力?是不是我該更加強勢一些呢?如果我的雙手有最後一口救命的水,而你因為絕望與恐懼而拒絕張開你的嘴讓水喝下,我到底還能做些什麼?我知道要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生命有生命自己的選擇,但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殘忍的讓我無能為力呢?
「親愛的媽咪,我還可以為妳做些什麼嗎?」
家庭的糾葛關係與每個人的情緒起伏交錯,其實是照顧過程最為痛苦的一塊了,但我好像讓自己又更加的艱難了一些:雙性戀身份。如果媽媽的生命盡頭不遠了,我到底要不要跟她出這個尷尬的櫃呢?如果我能現在找個男人結婚生小孩,媽媽會好嗎?如果我出了雙性戀的櫃,為的是什麼呢?記得『其他人』這部影片嗎?不想讓另一伴成為剩下的其他人,但不管在家祭或是公祭,如果伴侶關係沒出櫃,只能說是我的朋友,那終究,也只是之於我媽媽家人以外的其他人了。原來那麼多與家人互動的過程與關係的建立,那麼多的心理排演,不斷地的刻意安排,最終,我對於同性伴侶的位置也還是無能為力。
但我說了,這是一份大「禮物」。
故事的最後,媽媽還是離開了。過程中有諸多的來回議題,迷惘、難過、不捨、憤怒、選擇、猶豫、徬徨、無助、逃避、面對...好多的數不清,但我似乎現在了解了一些什麼。我絕對不會說走完了這次,我就豁然開朗,茅塞頓開了所有事情,我依然翻不到解答。因為我知道,生命的有限與無常,我終究沒有準備好的那一天。但是我至少在我媽咪還在的時後,藉著抱她起身走動而成為了一個最貼身的擁抱;家裡的經濟允許了我可以在最後的日子辭職在家陪伴老媽,雖然有些情勢所逼但卻也是我的甘願如此;因為她的虛弱與要求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幫她按摩,陪她說說話,陪她走上一段路;在最終的那一刻,我擁有了最幸福的時光--我看著媽咪吐出最後一口氣。
回想著這一路到現在,一年半再加上媽媽走後的三個月,無數次在車內哭、在房間哭、在洗澡時候哭、在路邊哭、在心裡哭、在別人面前哭,重複著不知道第幾次的故事敘述早已經麻木了,而「陪伴與照顧」的議題還是不斷的夾在「甘願」與「不甘願」中間遊走,從來就沒有一次的經驗是絕對的,也沒有一次的過程是不窒息的。試問我自己,若時間能倒帶讓我再走一次,我能不能走得更好?我不認為我可以。關於那些未來的想像,依然還是跑不過生命的變化,而穩健的大樹,也是因為生活的試煉而得以茁壯成熟。我想,對於生命的有限與無常,我沒有辦法活出兩全其美的答案,但至少,我還可以活出一個甘願且盡力的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