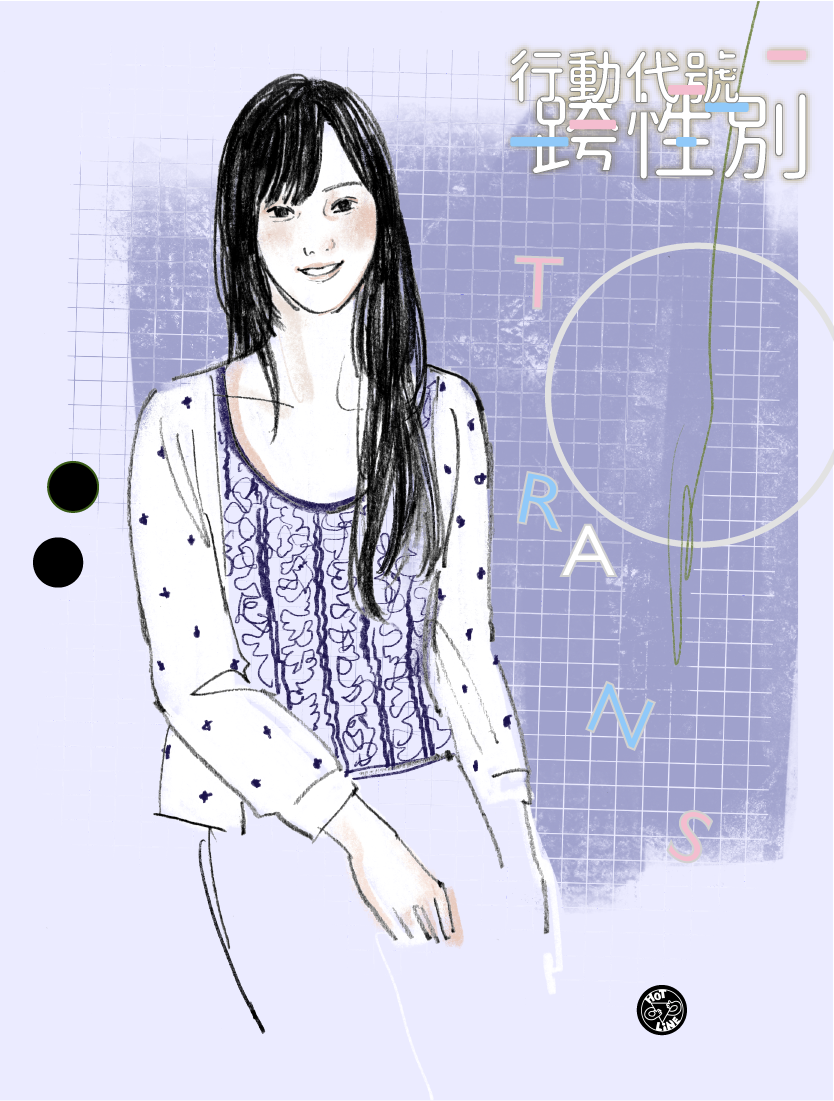
我的性別認同不是流動的:「他本來就在那裡了,感召著我去探索。」
阿甯是一位完成性別重置手術、身分證性別欄從男變成女的「跨性別」,性別認同對他而言宛如天命:
「我的性別認同不是流動的,他本來就在那裡了,只是我隨著成長慢慢去探索,把自己真正的性別描繪出來。」
過程中,阿甯從懞懂混沌,漸漸感受到性別認同的感召,想接觸卻恐懼害怕,
社會的惡意與污名荊棘般阻擋,讓「跨性別」猶如禁忌,卻也是在艱困的風雨中,雖千萬人吾往矣,最終破繭重生。
國小時期|不男不女,自我認同是周幼婷
從幼稚園開始,阿甯就不喜歡站著上廁所:「坐著尿尿,不會看到身體下面有東西,讓我覺得很自在。」
然而一直到國小,阿甯的性別認同都還很模糊,天生矮小瘦弱的他,一直都是班上最乾扁、小隻的成員,而三、四年之開始,同班女生慢慢發育,
同儕之間的性別樣貌開始有差異,同學們有了「男/女」的分別,氣質陰柔、身材瘦弱的阿甯,開始會被指稱為「不男不女」。
阿甯回憶,只有在音樂課時,會得到老師正向的鼓勵,「她會說我唱歌很好聽,並制止其他同學,捍衛我的性別特質。」不過這樣的支持遠遠不夠,
日常的關係排擠,始終讓他感到孤獨,尤其是體育課的躲避球環節:「我一定是站在內場,所有人丟球都針對我一個。」
積少成多的集體惡意,直衝那個自稱「人家」、毫無反抗能力、舉止怪異的學生而來。
而影響阿甯最深的卻是一堂健康教育課,老師拿出圖卡介紹女生第二性徵發育後的樣子,全班卻鼓譟的指著阿甯,異口同聲大喊:「你以後就會變那樣。」
「我也就這麼相信了,真的!」阿甯自嘲自己真的「很北七」,但其實當年心底也有一點點悸動竊喜,
期待有一天真的蛻變成美麗的模樣,「沒有覺得自己是男生或女生,那時候流氓教授很紅,我一心期盼自己會變成周幼婷。」
國中時期|終於發育,才發現自己竟然是生理男性
阿甯帶著對成長的憧憬畢業,卻發現國中又是另一處深淵,隨著班上男生的第二性徵也逐漸發育,他卻還是一樣弱不禁風、不男不女,與同儕間的差異就更被放大。
而年紀越來越大,對於資訊的接受也變得更複雜,當時選秀節目《超級偶像》當紅,沒有人想和他聊熱衷的選手,反而拿主持人利菁的跨性別樣貌,對著阿甯類比、揶揄。
當時媒體輿論帶著歧視的用著「變性人、第三性、人妖」等詞彙,社會對跨性別者充滿嘲諷、誤解的窺探,讓阿甯根本不敢多想自己與利菁是不是同一類人,
恐懼當前,更難梳理自己的性別認同到底是什麼。
到了國三,阿甯終於發育,急速抽高卻是另一場惡夢。國小健康教育課同學的玩笑,早就讓他深信不疑,以為自己會有一個女生的身體,
結果長高、長毛、男性性徵的成熟,才讓阿甯大夢初醒:「原來我是生理男性嗎?難道我不能長成周幼婷?」
「我從一開始對生理性別的認知就歪了,那個過程中,我雖然喜歡過男生,但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男同志,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男生。」
天真浪漫終成空,阿甯不得不承認自己生理上有個雄性身體,對於自己「是不是跨性別」的議題又變得更迫切、更真實。
高中時期|跨性別是禁忌,但要沒有雞雞才能辦婚禮
國中畢業,阿甯升上工業類型的技職學校,在那裡,他難得度過了求學歷程裡安逸、不被欺凌的三年,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真正認同自己是一名跨性別者。
「也是很白痴,就是在做白日夢,想到自己有一天跟喜歡的人結婚,有什麼是我理想中不可或缺的事情?」阿甯沈浸在粉紅色泡泡中左思右想,發現結論只有一個:
「不管最後跟誰結婚,我一定是要沒有雞雞的狀態!」卻也是因此,阿甯終於自我肯認了自己的跨性別狀態。
然而,又有一場健康教育課,讓明明身處友善環境的阿甯,再度意識到跨性別所受到的壓迫:
「護理老師播了一個很衝擊紀錄片,是國家地理頻道製作的《跨性別禁忌 The Transgender Taboo》」內容講述幾個跨性別者面臨的社會壓力,
無法明言的壓抑,為了維持生活的隱忍等等,「內容的深度遠超過高中生可以理解的範圍,播完之後老師也沒有多作解釋,讓那時候的我只有一個念頭 ——啊,跨性別是個禁忌。」
大學時期|開始用藥,卻也面臨關係霸凌的敵意環境
高中畢業,阿甯轉換到了護理科系就讀,依照校規,大學四年所有人都必須強制住校,阿甯也就此展開了自己的外宿生活。
離開家,有了自主空間和個人電腦,阿甯透過網路,大量接收有關跨性別的資訊,其中由椿姬彩菜所著《我是男校畢業的女生》被阿甯笑稱為
《第一次變性就上手》的攻略秘笈,參照著作者的歷程,他開始嘗試用藥,裝扮上把頭髮留長,衣著也更加中性。
外貌上的變化,使阿甯不斷處於「被出櫃」的窘境,從同班同學不舒服的探問,到周遭同儕獵奇般的窺視,以及學校老師、
行政人員無性別意識的尋找點名表示「那個男生怎麼還沒來?」「你這個女生怎麼在這裡?」
尤其是學校強制又明顯的「性別二分」設計,連日常走道都分男生一側、女生一側,而阿甯不管走哪邊都會被關切;
而宿舍男女分層,也會有不認識的女學生偷偷尾隨他,想知道這個不男不女到底住哪?也曾在自己寢室中聽到外人耳語:「這女的不檢點,竟然光天化日待在男生房間。」
稍微要好的同學跟他說:「你很有名欸,全校所有人都認識你。」阿甯卻只能苦笑回:「但我一個都不認識啊。」住宿四年,他是被孤立且凝視的異類。
好在,校園生活中還有一盞微光。阿甯回憶,自己求學過程中總是逃避體育課,尤其赤裸的游泳課更是最大罩門,大學期間,
他再度嘗試游泳,卻還是覺得痛苦難耐,於是到學校諮商中心尋求幫助,其中一位社工在聽完他的跨性別狀態與需求後,二話不說帶著他向體育老師說明,成功排除問題。
阿甯眼神閃起光芒,說那次經驗,是他第一次在校園體制內接受到實質的幫助:「從那之後,諮商中心就是我家,連校內工讀都是在那裡,
跟宿舍、教室相比,我更常待在諮商中心,在裡面我感覺很安全、很放心。」同時期,校外還有另一名跨性別朋友,能和阿甯互相傾吐、
帶著他學習穿搭化妝,於是,校內校外各有一股溫暖的支持力量。
然而,風波接踵而至,隨著用藥,阿甯的乳房開始隆起,四人一間的宿舍房,他總是趁無人時小心翼翼的曬乾內衣,卻再一次不小心遺落了胸墊,被同寢的兩位室友發現。
兩個大男生問阿甯「能不能摸摸看你的胸部?」還等不及愣住的他作出反應,已經一人架著他,另一人準備出手,幾乎無從掙脫時,第三位室友才已巨大的咆哮喝止,鎮壓即將不可收拾的場面。
「我一直到了諮商中心,跟社工講剛剛的過程,才開始哭。」社工安撫阿甯的驚慌失措,並主張向上呈報,試圖解決這長期以來的敵意環境,
然而,經過校內性平會的審議,卻只得到兩個方案:「一、跟原本的三個室友繼續住下去;二、另尋一個男室友兩人一寢。」
「我最後選擇跟原本的室友繼續住下去。」阿甯說,那時的自己已經從童年的樂天、學生時期的謹慎,變成徹底失望與封閉,
對人性毫無信任與安全感,便也不想再起換宿的波瀾,以及面對難以預料的未知。
進入社會|離開僵固壓迫的環境,活得像個人樣
大學畢業,阿甯成為護理人員。在第一間醫院,他總是獨自到另外的空間更衣;而到了第二間醫院,主管相對開明,
能夠理解阿甯的跨性別處境,在徵求相關女性同事同意後,阿甯開始在女性的更衣間更衣,不再因為性別而有差別。
阿甯回憶,從實習階段,就不像在學校一樣會頻繁的「被出櫃」,需要揭露性別的情境變得很少,於是就自在許多,
但一開始因為過去的創傷經驗,使自己封閉、不太敢與同事親近,多多少少影響了學習與表現,直到正向的經驗開始增加,他才慢慢找回開朗樂天的內心。
即便職場中還是有發生被出櫃的情形,或個別同事缺乏敏感度的事件,使得阿甯從此不在職場中出櫃,但總體而言,已經比過去在學校中舒適自在了不少。
變性手術|將自己置之死地,然後璀璨重生
2018年,25歲的阿甯獨自前往泰國進行性別重置手術。
即便母親大力反對,兩人在出發前大吵一場,母親稱他會變成「太監」,「我沒想到我一輩子被說泰國人妖,現在還要被說是太監,
好像我的性別認同跟需求從來不被看見。」把好不容易的跨性別實踐全盤否定,粗暴化約成失去性功能的男性樣貌。
但機票、住宿、醫院都都安排好了,箭在弦上,熱線跨小組的夥伴鼓勵阿甯:
「當你上了飛機,台灣的一切你都不要想,平安再說。」成了最大顆的定心丸,讓他整理心情,重新準備手術。
手術前,阿甯反覆告訴自己:「就當你要死了、就當你要死了、就當你要死了⋯⋯」直到手術醒來的那一剎那,即便麻醉還未全然消退,
內心卻早已激動得難以言喻,因為在麻藥抹去意識之前,他也偷偷在心裡默念:
「如果手術後我還活著,那一定就是重生。」
而帶著不一樣的身體回到台灣,阿甯回憶,到戶政事務所換身分證時,承辦人員非常友善,卻根本搞不清楚這類型的換證的業務該怎麼辦,
對方不斷打電話聯繫確認,頻頻致歉,「這一天我熬七年了,在這裡坐三個小時算什麼?」
在換證以前,阿甯一直以為換證的當下會感動大哭,結果沒有,反而回家倒頭大睡特睡:「真正難的是一路以來的事情。」
關於母親|從相愛相殺,到漸漸理解
手術後,阿甯在泰國待了一個月,傳訊息向母親說:「我好想你。」
「我媽媽也說她很想我。」終於在日常問候中漸漸破冰,回想當初開始用藥時,母親和這次手術的態度一樣,從直接忽視的逃避,到最後一刻爆炸大怒。
而細細理去言語中的尖刺,會發現中間藏著柔軟的愛,「我媽媽那麼反對,其實就是覺得 —— 泰國人妖會短命。」
而當刻板印象、污名與恐懼,隨著日復一日的互動與溝通漸漸鬆動,就能相互理解。
「我自己從光是用藥到手術就走了七年,我媽媽同樣也是只有經歷這七年。」
阿甯體認到理解需要時間,如同和自己和解一樣,需要緩和不躁的,給彼此空間與耐心等待。
自我認同|我是一個「跨性別」
醫療對於性別樣貌的介入,終究有極限。阿甯體認到自己不是跨越成女生,而是一個「跨性別」。
「重要的是『跨越』本身,整體歷程所帶來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如果今天一出生就是順性別女性,
那生命必然經歷一個截然不同的旅程;阿甯強調,正是因為自己的必然要面對的跨性別歷程,使自己經歷到無法替代的「好的事情」。
尤其是那份「真正被人接納的感覺」,如果今天只是順性別女性,或許就不會面臨這麼巨大的焦慮,
「那種連表明『我是誰』都會被指責的感覺。」,卻也是在這樣的逆境之中,找到能接納自己的人,才會感受到那般無與倫比的美好。
也如同變性手術後,甦醒的過程裡,彷彿是薛西弗斯終於將巨石推上巔峰,反覆磨礪往返終於得場所願的暢快油然而生,
「你過去很難真的想像這件事情會實現,而當你終於走到這一步,真的在醫院醒來,雖然很痛,但卻只有無以名狀的感動,覺得自己幸運的,再活一遍了。」
認同小物|跨性別鑰匙圈,不忘這趟歷程冒險
阿甯拿出對自己別具意義的小物 ——「跨性別鑰匙圈」,
解釋道:「它就像是一到指引,指引我不斷探索自己的跨性別認同;同時也給我強烈的歸屬感,
如果有一天我忘了這趟旅程的所有回憶,那我就徹徹底底是另一個人。」
對阿甯而言「跨性別」是他生命的脈絡,也是最重要的歸屬,而鑰匙圈,則默默導引著通往自我的方向感。
